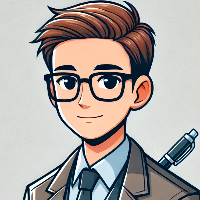Modeling the conductance and DNA blockade of solid-state nanopores
S. W. Kowalczyk, A. Y. Grosberg, Y. Rabin, et al.
摘要
我们介绍了固态纳米孔的离子电导G的测量和理论模型,直径为5–100 nm,并在孔中插入有或没有DNA。首先,我们表明必须包括访问电阻以描述电导,特别是对于较大的孔径。然后,我们为沙漏形孔的G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与我们的测量非常吻合而没有任何可调参数,并且对圆柱近似的改进是一种改进。随后,由于将DNA分子插入孔中,我们讨论了电导阻滞G,我们在实验上研究了孔直径的函数。我们发现G随孔直径减小,与预测恒定G的早期模型的预测相反。我们比较了G的三个模型,所有模型与我们的实验数据提供了良好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