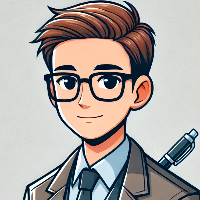R. T. Perera, J. K. Rosenstein
摘要
纳米级工作电极和小型电分析设备是探测分子现象和进行化学分析的宝贵平台。然而,集成到小体积电解质中的金属电极固有的近距离会使经典的电分析技术复杂化。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扫描纳米移液器接触探针作为模型微型电化学电池,以证明在准参考电极上发生的反应的可测量副作用。我们提供了在没有任何电活性物质的情况下原位生成纳米颗粒的证据,并批判性地分析了这些纳米颗粒出现在工作电极上的起源、成核、溶解和动态行为。为了准确解释纳米级电化学实验的结果,认识到在受限电化学电池中使用准参比电极的意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