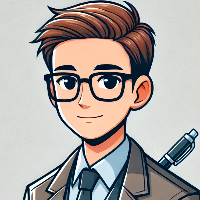Physical Model for Rapid and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Nanopore Size via Conductance Measurement
C. Wen, Z. Zhang, S-L, Zhang
摘要
纳米孔已用于各种生化和纳米颗粒分析,主要通过表征通过孔的离子电流。然而,目前固态纳米孔的尺寸测定在实验上繁琐且在理论上无法解释。在这里,我们通过引入有效传输长度 Leff 建立了一个物理模型,对于对称纳米孔,该长度测量的是电场最高的纳米孔中心到电场下降到最大值的 e-1 的纳米孔轴上点的距离的两倍。通过,推导出一个简单的表达式 S0 = f (G, σ, h, β),以代数方式将最小纳米孔横截面积 S0 与纳米孔电导 G、电解质电导率 σ 和膜厚度 h 关联起来,β 表示由孔制造技术决定的孔形。该模型与石墨烯、单层 MoS2 和超薄 SiNx 薄膜中纳米孔的实验结果高度吻合。通过将模型应用于微米级孔隙,验证了该模型的通用性。